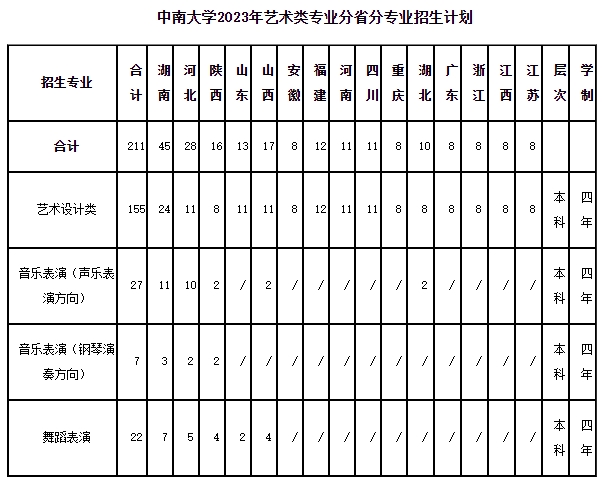超現實主義畫派1(超現實主義畫派中傾向于抽象的畫家是)
早在布列頓(AndreBreton1896-1966)和沙拉(Tzara)在達達主義問題上發生沖突之前,布列頓就同詩人菲利普·索波爾特共同開始通過自動寫作法探索心理經驗中的想象層次了。《磁帶性的原野》是他們在1920年發表的第一件作品。作品中因對理智的抑制而產生的隱喻奔涌而出,其中也有些令人過目難忘的視覺隱喻。不久,藝術家和作家都對揭示這種"真實的思想過程"(布列頓在第一篇超現實主義宣言中所下的定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篇宣言發表于1924年下半年,但布列頓1928年在一篇重要論文《超現實主義與繪畫》中才肯定了超現實主義藝術的重要性。然而在這篇宣言的注釋中,他號召人們注意當時那些可能與文學超現實主義有聯系的藝術家,其中有幾位"野獸派"或"立體派"的畫家:馬蒂斯、德朗、勃拉克和畢加索。他們的作品不太符合布列頓為超現實主義下的定義:純粹的心理自動法。不過,他們中間還有一位意大利畫家,名叫喬治·德·基里科,他是短命的"形而上畫派"的創始人主將。這個名稱是他和未來派畫家卡洛·卡拉為他們1917年在費拉拉城創作的作品而起的。基里科1911年至1915年一直住在巴黎,他的畫很受阿波利奈爾的崇拜。阿波利奈爾1918年寫的劇本《蒂里西亞的乳房》就是以"超現實主義戲劇"為副標題的。對于首次使用這一術語,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追求語言和心理學的大師和詩人來說,他如此看重基里科的才華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基里科的早期作品也象阿波利奈爾支持的立體派畫家的作品一樣,打破了繪畫的視覺邏輯常規,獲得了更加出人意料的效果。
基里科筆下的世界乍一看來具有一種秩序井然的假象:線條利落,色彩鮮明,光線柔和,形式上非常醒日。然而,人們發現這個世界里的空間,也許還有時間,已經脫離了它們一向遵守的整齊界線。在《一位皇帝的邪惡的創造力》(1914-1915)中,建筑物內景、桌面和各種物體的幾個透視點的非邏輯性并列會引起心理上和視覺上的不舒適。異化感、失落感,與其他人類隔絕的孤獨感,對自己處境的不踏實感以及由此產生的對自我特質的懷疑感十分強烈。人們怎樣才能知道他身處何地或置于前景的是什么物體呢?即使我們知道它們是什么,我們也仍然不得而知它由何人為何因帶來此地的。標題是另外一個令人困惑的因素。它什么也沒有說明,但卻引起了沒有滿足的期待感。其它的標題,如《秋日午后之謎》或《離別苦》傳達了由空間暗示的聯想。布列頓之所以對此十分欣賞是由于這些空間的比例和透視同我們的夢境很相象。在此之前,繪畫史上還從示有人在全能的夢中和毫不相干的思想過程中按照布列頓的定義把世界建筑在"一個至今被忽視的某種聯想形式的超現實"之上。對布列頓來說,繪畫中真正的超現實主義的因素,可以通過將互不關聯的事物并列在一起而產生。正如超現實主義者康特·德·勞特曼在《馬爾多拉之歌》(1888)中使用的暗喻那樣:"……美麗如縫紉機和雨傘在解剖臺上偶然相逢。"實際生活中的這類偶然相逢我們稱之為"巧合",布列頓為這種情形下的定義是"客觀機遇"(Objectivehazard)。
1915年,基里科開始畫機械動作的人物。空心人似乎是用卷曲和折疊起來的麻布制成的,就象裁縫使用的假人模型:蛋形腦袋,面目全非,由東倒西歪的木條支撐。無論是作《赫克托耳與安德洛瑪刻》還是《行吟詩人》,他們都只是欲望的幻影,沒有面龐,也沒有內在的活力,既不能動,也不能愛。他們是杜尚的機械式的新郎娘的同輩人,而且也進一步擴展了描寫機械式情欲的蒼白的肖像畫法。
到了1924年,當布列頓公開宣布超現實主義是通過自動聯想,通過內心生活的基本現實去加以發現的一種手段時,基里科已摒棄了早期作品中的那種魔幻靜態并且試圖象當時的德朗所做的那樣,恢復具有非人格化宏偉氣勢的文藝復興鼎盛時期的風格。但這種努力最終一敗涂地,使基里科從此陷入了已過時的那些傳統技巧和主題之中。
除了基里科外,參加過1925年6月在巴黎舉辦的首次超現實主義畫展的畫家誰也沒有掌握所謂的"連貫的超現實主義風格"。畢加索和阿爾普在藝術上已趨成熟。馬宋和米羅正在從再現轉向更為抽象的形式處理。而當時在包浩斯學院的保羅·克利還根本算不得嚴格意義上的超現實主義者。在每個人的作品中,包括畢加索在內,基本的藝術要求決定了繪畫和雕塑形式的特點。只有馬科斯·恩斯特,一如我們所見,已經在他的達達主義作品中對表現性的內容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特別是在他的拼貼畫中。1922年,恩斯特在巴黎定居后繼續設計了一系列拼貼"小說",其中的幾句正文以解說詞的形式寫成,和插圖一樣神秘。最著名的有《百頭婦人》(LaFemmecenttetes,法語為雙關語,也可譯為"無頭婦人")。這幅畫可能講的是杰米諾邪惡的一生和淫蕩懷春的女主角。用恩斯特本人的話來說,畫中的一系列顛覆性心理意象是由"方法和暴力"組成的。
恩斯特并沒有發明拼貼術。在立體派畫家手中,拼貼術一直是為加強畫中的審美現實感所使用的一種技巧。但由于恩斯特使用的媒介不是傳統的畫筆和顏料,而是具體的實物和原料,因此他自己做出了兩項發明。第一項他稱之為"frottage"(拓摹法)。這是他在1925年的一個黃昏看到剝落的地板上不規則的木紋時產生的一種幻覺迷戀。他認為他可以把這些幻覺用鉛筆永久性地拓摹下來,并且繼續用它原料如樹枝、樹葉、線繩等進行試驗。這樣制造出來的形體雖然經他的手稍加夸張了一些,但他因此創造出大量嶄新的形象。1926年,恩斯特發表了一本作為"拓摹法最初收獲"的畫冊,題為《自然史》。由于這種方法,根據恩斯特的定義,允許他用恰當的技巧強化"想象領域的過敏必并同時排斥一切有意識的思想傳達(理性、超味或道德)",所以他認為這是自動寫作法的"真正等量物"。
恩斯特的第二個發現是他同西班牙的超現實主義者奧斯卡·多明蓋茲(OscarDominguez1906-1957)共同做出的。恩斯特進一步將藝術家的有意識努力貶低到自動效果和偶然效果之下,并把這種技巧稱之為"decalcominia"(移畫印花法)。當顏料壓敷在仍然潮濕的畫布上之后,他發現一旦壓力消失,顏料會呈現出神秘的形狀,暗示出大量嶄新的形象。經過藝術家進一步的強化和調整后,這些形象對表現森林景象顯得格外有用。1927年后,森林風景畫在恩斯特的作品中占主要位置。森林始終能使恩斯特產生恐怖的聯想。在那些濃密的樹蔭深處和神秘的景物中,人的理性已不再是至高無上的了。"夏天對森林有什么意義?"他問道。它意味著末來:"這是濃蔭能夠將自身變為詞語,被賦予歌喉的生物將在零點勇敢地尋找午夜的季節。"
恩斯特用拓摹法和移畫印花法技巧處理自然景物的高峰出現于法國淪陷后他客居美國的那段時期。1943年,他在亞利桑那州度過了一個夏天,隨后又在那里居住了幾年。西南部無垠無盡的廣袤以及色彩斑斕的巖石造型開始在他的畫中出現了。但它們是以狂暴的面目出現,暗示人類感情的不和諧。這種不和諧在早期的幻想風景畫中曾表現過。在《沉默的眼睛》(1943-1944)中,陰冷的水池和奇形怪狀的石墻被出色地記錄下來,但它們被一些對人類懷有敵意的東西包圍著。
德國-瑞士畫家保羅·克利(PaulKlee1879-1940)雖然也參加了巴黎的第一屆超現實主義畫展,但他一直都沒有成為這一運動的正式成員,而且他的藝術也很難簡單地以"超現實主義"一詞冠之。用一個人們熟悉的詞來說,克利是一個當代技巧的"百事通",是一個掌握了大多數技巧的大師。1914年以前克利在慕尼黑居住,在那里結識了康定斯基和馬克,并在第二屆青騎士畫展上展出了蝕刻畫和素描。戰后他曾在魏瑪和德紹城的包浩斯學院執教十年。就這樣,他身體力行,從實踐中掌握了表現主義和構成主義的原則和技巧,并在從巴黎到柏林的往返旅行中掌握了其它流派的理論和實踐。他用英語發表的課堂筆記《思考的眼睛》(1961)證明他曾潛心研究過視覺構成的基本問題。但他在研究古今大師們時,表現出了詩意般的洞察力和出色的闡釋才能任何斷開平面和重新組事平面的立體主義嚴肅技巧都逃脫不了他那冷嘲式的智慧。這種智慧隱藏在他給予許多作品的神奇標題中。1930年,克利離開了包浩斯學院到杜塞爾夫學院任教。但三年后他被納粹解雇,以后便在瑞士居住直至去世。這期間他畫出了一些他以前從末畫過的大幅畫,不僅是畫面大,而且令人驚懼。在這些畫中,早期作品中幽默的人物形像變成了憔悴的表意文字,指向即將降臨的恐怖事物。
以超現實主義畫家的面目出現在最顯赫人物,無論是其藝術或自覺的不規則生活,是加泰隆尼亞畫家薩爾瓦多·達利(SalvdorDali1904年生)。達利的畫中有構成夢幻形象的最尖銳的明確內容;使用的是早期歐洲現實主義大師,特別是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家維米爾和同期的西班牙畫家如委拉斯貴支的表現技巧。按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用這種方法記錄了"具體的無理性的形象和最專橫的精確憤怒"。他所執著追求的形象是由妄想狂誘發的形象。在他所有的早期作品中,這種形象是他最理想的形象。但在這種形象的表面,理性和顯示這種形象的含混、非理性之間,往往有一種令人不安而又不可抗拒的沖突。達利比其他任何畫家都更能通過最具體的形象認識到所謂的"超現實"(至少完全不同于日常經驗)。布列頓認為,這種超現實可以"迄今被忽視的某種聯想形式"中找到。極其重要的是他在一個特定的形狀中看出多種形式的非凡能力。《一張臉的閃現和海灘的水果盤》(1938)雖不是他最富有"妄想狂性質"或最狂暴的作品,但它是視覺上效果最復雜的作品這一。看畫的人每一刻都發現自己在穿過或透過至少四個層次的交織形體觀看。餐巾一樣展現的海灘占居前景,上面安放著一個巨大的果盤。果盤的圓和邊緣化成了一個女人的眉毛和面龐,她的頭發同時變成了盤內的水果和狗身上的衣服的圖案。狗的身體也同樣由許多毫不相干的成份組成。例如,狗的口絡也可以被看作海灘和波浪遠方的一個石穴。